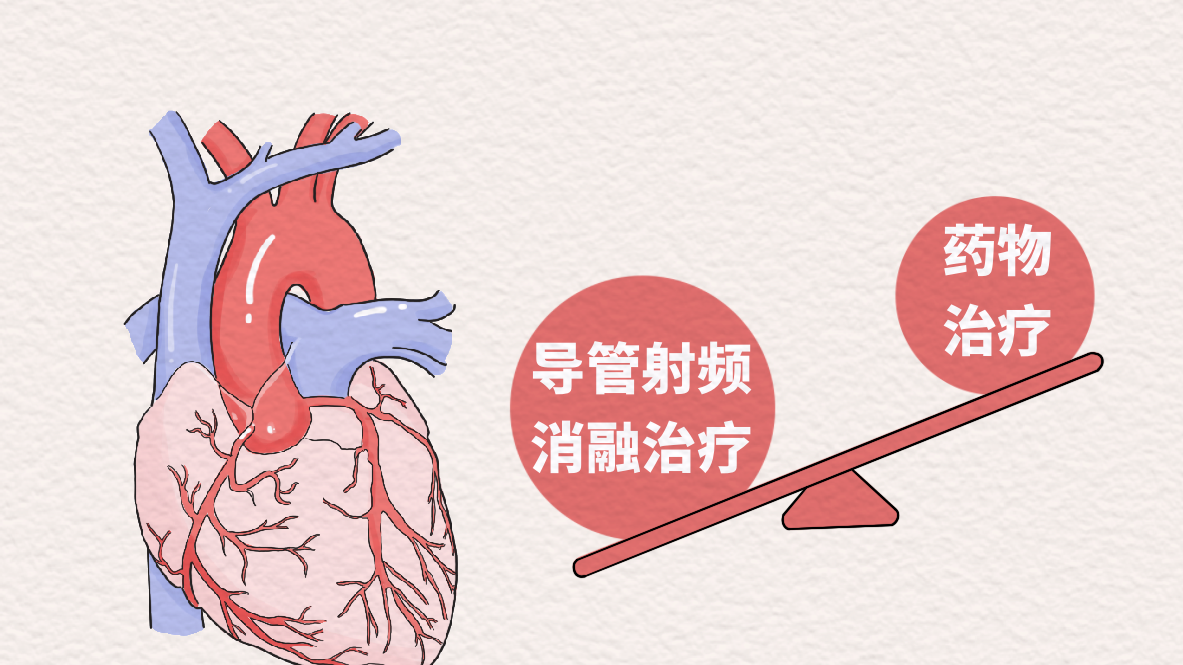吃过那么多火锅还是偏爱家楼下这一口


火锅对于重庆人来说,是生来便自带的社会属性。一锅沸气腾腾的红汤,承载了太多喜怒哀乐和千奇百怪的故事。

我对火锅的记忆大概是从上小学开始的,那个时候家里不宽裕,下馆子是件极其奢侈的事。关于火锅的初体验,是在逼仄的厨房,围着灶上那口黑漆漆的大铁锅,站在锅边顶着热气烫菜。荤菜只有毛肚,鳝鱼和午餐肉,素菜一般是豆芽、鸭血和包包白。我妈从不偷懒,每次煮火锅都会自己加菜籽油、郫县豆瓣、姜蒜把买来的底料炒香。

在没有抽油烟机的年代,一顿简陋的家庭火锅,让30平米的房子一整晚都弥漫着牛油香。后来,家里一个月大概有两次下馆子打牙祭的额度了,但几乎每一次都是去家楼下的火锅店。那时候店堂里的桌数不多,很少有人单独烫一口锅,吃火锅流行“打组合”,“镶起吃”成为一种行规。
几家人围烫一口锅,锅里放上九宫格,既方便分隔菜品,也方便大家各认各的格子。小桌子镶四人,大桌子镶八人,不镶满还不点火。

但不管怎么拼,和谁拼,吃起来都全无尴尬,专注烫菜之余,还能蹭点邻座的龙门阵听听,那样的场景,现在想来也是妙不可言。
再长大一些,重庆城内的火锅馆,店堂门前大多都有了一个“拖”字。四拖二,三拖一比比皆是,荤菜三块,素菜一块。两个人吃火锅不用再拼桌了,吃顿火锅的钱对家里来说也算不上太大开支了,但我常去的始终还是家楼下那家火锅,也许留恋的并不只是它的味道,而是来自早已面熟的老板一句邻居般的寒暄,和不大的堂子里陌生人挤在一起的热闹和亲近。
躲在九坑子一条小巷子里的“碗胖”,就是这样一家平易近人的社区火锅。

没有富丽堂皇的装修,没有名不副实的噱头,重庆人本就偏爱“苍蝇馆子”,有一种走到咔咔角角都必须找到,找到吃进肚子才算了事的执着。
大坪九坑子路20号,碗胖火锅不太规整的门面就藏在一栋居民楼楼下。四周弥漫着市井的烟火气,浓厚的火锅香味四散进满是岁月痕迹的阶梯石缝里。

正因为靠近住户楼,碗胖只营业到晚上10点,人均60元的价格在如今的火锅市场中已经不太多见。食客也心甘情愿为那一锅红汤压低了声音,喝酒划拳都多了几分自持。
碗胖就跟曾经我家楼下那家火锅店一样,看起来没有任何特色,这样不起眼的小店,还能做到每晚有人排队等饭,靠的只能是味道。重庆好吃的火锅那么多,真正要杀出重围必须得有几个能打的特色菜。这一点,碗胖没让人失望。

猪肝
活了三十多年,第一次在火锅店烫猪肝。猪肝原本比牛肝口感更嫩,但片起来比牛肝、腰片更难,新鲜的猪肝要出浆,滑腻,十分考验刀工,所以大部分的火锅店根本不敢尝试。

碗胖的猪肝绝不过夜,每天限量3斤,只有10份,有幸吃到还得惜缘。涮好的猪肝薄薄一片,没有丝毫腥味,入嘴全是嫩滑鲜香,每一口都爽到不行,再配上老板妈妈手工特制的干油碟,更是销魂。如果你还嫌不够辣,颜色更深的特辣干油碟专治嘴嚼。
墩墩牛肉
精选西冷牛肉提前用黑胡椒汁码好,再撒上黑胡椒粉切成厚实的条状。本以为这种size的牛肉会容易煮老,没想到一口下去还能咀嚼出肉汁,浓郁的黑椒和锅底的麻辣全浓缩在这块牛肉里,吃火锅吃出了牛排的感觉,也是服气。

肥肠
像我这样明明胆固醇超标还死性不改迷恋内脏的人,每次都习惯点份肥肠来检验这家火锅店的水准。有些店的肥肠压制时间过长,在锅里稍微煮一会儿就弹性全无,失了嚼劲,有些店的肥肠卤得过久,一不小心就喧宾夺主抢了锅底的鲜香。

碗胖的肥肠先压后卤,压制和卤制的时间把控得精确,卤味不会过大掩盖火锅味道,入口时却又有丝丝卤香。肥肠清洗得相当干净,几乎没有多余油筋,吃起来软糯入味,过瘾。
鸭血

跟猪肝一样,鸭血也是每天限量供应。不夸张的说,他家的鸭血真的是我目前为止吃过最嫩的。鸭血都是每天直接从旁边菜市场端来的.每天到底能有多少份,全凭运气。吃他家的鸭血,记得冷锅的时候就下菜,试过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的。
插播一个小tips:

碗胖隔壁还有个卖红糖小汤圆的老头儿,没有摊位,电话订购。在这种冷到怀疑人生的天气,简直是烫火锅的完美伴侣。
为什么叫碗胖?
那一天我一边吃着火锅一边好奇为什么这家店取名叫“碗胖”,最后终于在老板刘俊那里得到了答案。刘俊是个土生土长的80后重庆崽儿,之所以把店取名叫碗胖,是因为他曾经一顿能吃七碗饭,人送外号“碗哥”。“加上我长得又胖,所以就叫碗胖了撒。”刘俊笑得爽朗。

对于重庆人来说,火锅面前,人人平等。不管你是朝九晚五拿着死工资过活的打工仔,还是年薪百万开着豪车的大老板,为了这口热辣一样只能乖乖排队。就像你很难想象,如今通宵炒料炒到手软的刘俊,曾经从事的是一份工资不菲的法律工作。

临走时,看着刘俊一脸笑容手拎一瓶啤酒,和不同桌的食客热情攀谈的模样,我仿佛看到了记忆中家楼下那家火锅店的模样。也许,这就是我们钟爱社区火锅的原因。


 无障碍
无障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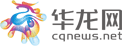
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
手机阅读分享话题